|
贺绍俊
北京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
在遥远的记忆中,乡下的时间总是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地挪。
北京就不一样了。
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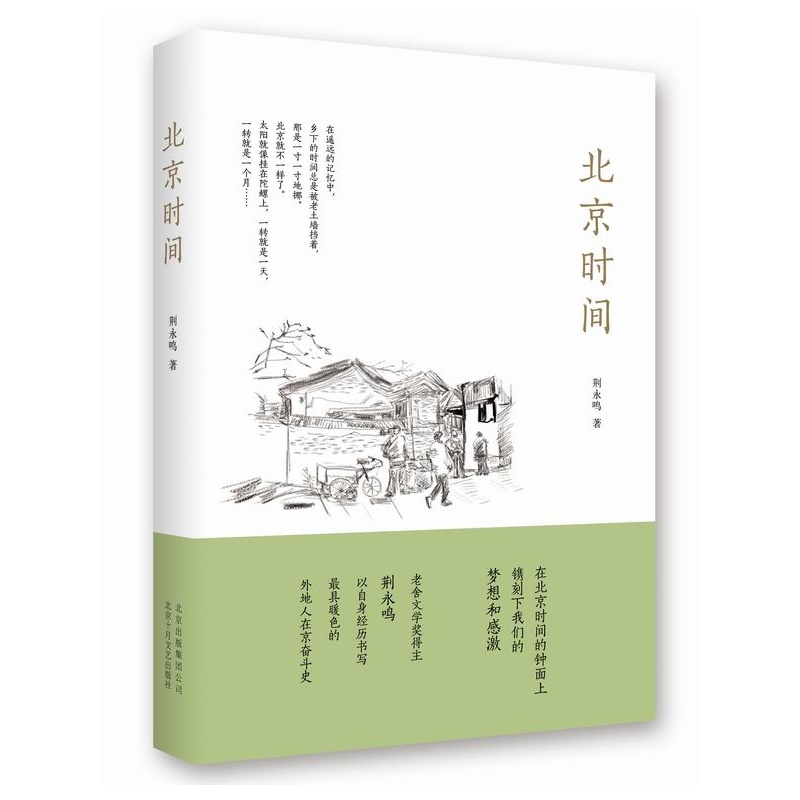
《北京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版
我突然发现,荆永鸣一不小心竟成为哲学家了——这样说,丝毫没有嘲笑他的意思,因为荆永鸣是一个生活实感特别强的作家,他不爱做那些与生活实感相脱节的玄思,他又是一个最实诚的人,从来不愿意卖弄一些高深的词汇。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荆永鸣在尽情体验生活的同时不免触动了深深蜇伏的哲学。比如他这些年自觉地以一个外地人的眼睛来看北京胡同,看着看着,就看出了时空的关联了。他先是在《北京邻居》上表达了他的空间感,接着他又从空间推演出时间来,于是就有了我最新读到的《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是从《北京邻居》以及此前的《北京房东》挪移过来的,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挪移,因为在时间的发酵里,空间发生了变异。在荆永鸣的感觉里,“北京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他以这句话开始了小说的叙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还提出了时空弯曲的结论吗?荆永鸣似乎在证明爱因斯坦的论断,相对于乡下时间,北京时间肯定发生了弯曲,不然它为什么会过得快一些呢?在荆永鸣的笔下,北京时间是这样发生弯曲的:“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
荆永鸣的小说被称为“外地人”小说。多年以前,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市的荆永鸣一头扎进了北京城,用一个外地人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北京,也带着一个外地人谦逊的姿态与北京人打交道。他将一个外地人的观察与体验写进了小说,并获得了良好的反响。但时间会让人发生变化。我们从荆永鸣的这部小说里看到了变化的轨迹。最初,荆永鸣一头扎进北京城,也就随着北京时间转,所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三个月就过去了。荆永鸣说“时间越快,我反倒觉得越是难熬。”表面上看,荆永鸣讲述的是他一个外地人到北京来打拼的艰辛,故事也基本上是沿着时间的顺序一路发展下来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我”(不妨就将“我”看成是荆永鸣的自我表白)不满于在北方某煤矿的平淡生活,毅然辞职,与妻子一道蹬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北京,他们开了一家小餐馆,又在附近胡同里租了一间平房住了下来,几年下来,餐馆生意越做越好,他们与胡同邻居的关系也处得很融洽,荆永鸣给我们讲述的都是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人际交往中的小摩擦、小风波。但在讲述中,荆永鸣的时间观念悄悄发生了变化。最初,他是拼命追着北京时间的速度,他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后来,他逐渐适应了北京时间,也就发现了北京时间的“弯曲”:当人们为了衣食住行“正在嘈杂拥堵的马路上慌慌张张,甚至是寻觅挣扎”时,在北京的公园里到处都是“玩着的”北京市民。于是荆永鸣放慢了脚步,他饶有兴趣地琢磨起北京的时间和空间。像这样的感慨也只有对生活有了一种顿悟才能获得:“生活杂乱纷繁,剥去层层外表,你就会发现,人只是活在时间里。当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人也在不断地变化。有些人在时间里变老,有些人在时间里死去。”他尤其对于北京人既离不开北京的时空又想摆脱北京时空的束缚的复杂心态有着透辟的书写,比方他写到了在北京郊区的漂亮的小洋房,这是不少北京人为追求生活质量而买下的别墅,荆永鸣在小说中写道:
城里的有钱人大都向往乡下的生活。他们喜欢乡下的天空,喜欢天空中的白云和飞鸟;喜欢农田,喜欢庄稼,甚至喜欢那些脏兮兮的羊群。空闲的时候,他们喜欢开着奔驰宝马到城市以外的乡下去兜风,漫无目的的欣赏着窗外的乡村风景,他们把山沟里的那些石头房舍、泥巴小屋看成是一种美,甚至会产生一种兴奋不已的向往:“要是住在里边,多肃静,多有意思啊!”然而,喜欢是喜欢,向往归向往,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闹哄哄的城市,把家搬到乡下去享受那份安静。于是,在城市边缘的郊区,就有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漂亮洋房,像童话般地半隐在丛林之中,或立在草坪之上——它的功能不是供人生活与居住,而是为了让时间变得缓慢起来,把人与人之间隔离起来,其目的就是给人提供一种幽静、隐密、而又十分宽敝的私人空间——这样的房子,被周围的乡下人叫作“别野”,它们的主人则称它们为“别墅”。
“它的功能不是供人生活与居住,而是为了让时间变得缓慢起来,把人与人之间隔离起来,其目的就是给人提供一种幽静、隐密、而又十分宽敞的私人空间。”这分明就是一种关于时空的哲理表达。
北京时间就像是发酵剂,又像是加速器,又像是魔棒,它作用于在北京时空下生活的每一个人。即使是胡同里的普通百姓,也挡不住它在你身上施展的魔力。北京时空发生的变化,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变化之快和变化之大,人们都不曾料想。但在变化之中我们也许就失去了什么。荆永鸣对这一点似乎看得更清楚,也更在意。即使作为一名外地人,也会对曾经触摸过的北京时空生出感情。他在小说中写到一个细节。“我”曾经租住过的那条胡同拆迁了,那些北京邻居也各自分散了。有一天,在王府井大街上,“我”遇到了一位老邻居赵公安。荆永鸣写到这个细节时,特意让时间停顿下来,让这两个人物好好地酝酿了一番感情:
我们并排坐在马路牙子上,一边吸着烟,一边说话。对面儿就是甲32号院的大概位置。眼前的一座商务大楼和周围高低错落的仿古式商业建筑,它们属于一条消失了的胡同。当时我的赵公安都沉浸在一种共同的回忆里。有一会儿,赵公安还指指点点,他说哪个地方是甲32号院的大门口,哪儿是他的家,哪儿是冯老太太的小卖店……如数家珍。我注意到,这时候的赵公安已经完全沉浸在一种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中,他眯着那双小眼睛,脸上的表情竟温柔得像个孩子。只是,眼前的一切已非实物,那个真实的时间与空间都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靠想像还原它在记忆里的样子。
此时此刻,他笔下的人物带着孩子般的温柔表情,回忆着往昔,只是“眼前的一切已非实物,那个真实的时间与空间都已不复存在”。
说到底,北京时间是一个已将现代性发条上足了的时间,荆永鸣却用一种日常生活的时间来校正它,日常生活的时间是被亲情和友情一点点往前挪移的时间。北京时间的加速度带来了巨大变化,对这种变化荆永鸣还有所保留。他让小说中的“我”有一天看到被轰轰烈烈拆掉的“伦贝子府”如今当成了一处停车场。他感慨道:“置身在这样一片‘寸土寸金’的废墟上,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确切地说,是我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全都错乱了。”但无论时空如何发生变化,荆永鸣让“我”的亲情和友情始终不变,“我”与赵公安,与方悦、方长贵、老杨头,那些曾经的邻居,始终保持着一种情感的牵连。这也许就是荆永鸣写《北京时间》的真实意图,无论北京时间怎么“弯曲”,他希望能用浸透了亲情和友情的日常生活时间,对北京时间加以校正。这或许就是荆永鸣所说的能够打开“时间之门”的钥匙吧。
|